近日,沉寂已久的华晨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传闻宝马中国以16.33亿的价格收购 “中华”品牌汽车生产相关部分资产及华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要明确的是,宝马中国收购的仅是土地、厂房、设备等,不包括生产资质和中华品牌。
实际上,华晨这座大夏已经坍塌很长时间了,不过这次被宝马收购部分资产还是让人唏嘘不已。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华晨的落败究竟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造车得“术业有专攻”
在汽车市场,费迪南德·皮耶希、恩佐·法拉利又或者迪斯、丰田章男这些缔造一个个汽车王国的大师们,无一例外从汽车相关专业毕业,将对汽车的热爱融入到骨血之中。即便是徐留平、竺延风、尹同跃也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根汽车市场数十载。一句话,对资产、技术高度密集型的汽车行业必须要“术业有专攻”。
而在华晨的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两位管理者——仰融和祁玉民都是汽车门外汉。
先说仰融,毕业于西南财大,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个“以造车为手段,以金融为目的”的资本狂人。
在仰融执掌华晨的十余年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买买买”,先是花了数十亿元,通过控股、独资的形式,把一家孤零零的金杯客车厂发展为囊括小客车、轿车、SUV、皮卡的整车制造、发动机生产、零部件供销和汽车分销在内的庞大汽车集团。
紧接着仰融四面出击,一度掌控了国内外六家上市公司,各种关联企业158家,其中控股138家,形成了当时总市值超过300亿元的华晨系帝国,因此得了个外号——“中国第四汽”。
但这个时候,金玉其外的“华晨帝国”内里其实仅有金杯海狮小客车这么一个孤单影只的盈利点,缓慢的资金积累显然无法支持华晨,准确的说是仰融的肆意扩张。所以,当宁波市政府特许仰融成立建筑公司,参与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盈利的时候,造车的仰融竟然答应了。当时,很多人干脆说,华晨本质上应该是一家投资银行。
不可否认仰融给华晨帝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荣光,但是拿金融的高杠杆玩转造车自然是行不通,这也为继任者埋下了隐患:一是长期亏损,在2005年末,华晨一年的亏损额就高达4亿,工厂几乎全面停产;二是混乱的体系,仰融时期的华晨仅承运商业物流的服务商就高达30多家,远超其他车企常见的两三家水平。
2005年12月履新的祁玉民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许是辽宁省国资委从仰融的“右倾”管理中汲取了教训,给华晨空降了一名标准的“政客”——祁玉民。翻开祁玉民的履历,起步于大连重工,从大连副市长的位置转任到华晨,担任一把手。
在履职的路上,祁玉民给家人发了一条信息:“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奔赴一个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单位,从事一份陌生的工作。”
“陌生”是造车零经验的祁玉民彼时最好的写照,但时不我待。对于政客而言,祁玉民信奉的是“人亡政息”的那一套,他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凌驾于自身的威权之上,为了摆脱仰融的影响力,祁玉民到华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炸掉之前仰融因为风水安排在办公楼前的一座山,又退出美股,树立威信。
随后,祁玉民为病危的华晨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曰降价。
仰融虽说需要为华晨的走弱负首要责任,但他的功绩在于成立了“中华”这个特殊而又必要的自主高端品牌,从今天来看极富远见。
不过,祁玉民不这么想,一是出于“凡是仰融赞成的我都要反对”;二是想以价换量,盘活华晨。于是乎,雷厉风行的祁玉民悍然发动价格战,中华尊驰下调4万,B级车的定位A级车的售价,华晨中华销量迅速飙升;再然后推出10万以下的骏捷,和低端车抢市场。
从当时的环境分析,祁玉民的做法无可厚非,坏就坏在祁玉民认为“降价”是唯一提升销量的良方。在此之后,华晨在以价换量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无论是后期的中华V3、还是V7都不可避免的走上了尊驰的老路,以至于仰融苦心打造、欲与“红旗”试比高的“中华”沦落为三线低端品牌。
二曰宝马。
祁玉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外号:“爱马士”。究竟有多爱,举个例子,2006年,宝马在上海设置了覆盖华东区域的销售大区,区域经理全部由宝马从德方派遣。同年,宝马华南大区成立,区域经理同样由宝马中国指派,原本华晨系掌握的渠道销售体系彻底宣告失守。有了先例,很快,华晨宝马的财务、行政、销售、市场、公关等部门的实际控制权便都掌握在了宝马手中。
本应强烈反对的祁玉民对此却三缄其口,听之任之。而针对华晨宝马首开先河,外资独占75%股份的实现,也有祁玉民的一份“功劳”。如此“宠幸”宝马,祁玉民的逻辑也很好理解,作为整个华晨帝国的“利润奶牛”,华晨宝马为祁玉民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政绩,他又为什么要苦心经营自主品牌中华,前人种树让后人乘凉?
不仅于此,从2006年起的三年间,祁玉民调整管理体系,同时出任金杯、华晨、申华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不仅大权集于一身,而且疏于人才体系的培养。倘若,最初的集权还有利于祁玉民解华晨的燃眉之急,那么在之后发展的过程中,再无忠言“进谏”,去修正一言堂之下的错误路线,就是政客祁玉民最大的失职。
可见,玩资本的仰融和玩政治的祁玉民,无一例外对造车缺乏敬畏之心,不熟悉市场,背离了行业发展规律,一意孤行,酿成了今日华晨中华的苦果。
而对祁玉民来说,如果不让不懂汽车的他来管华晨,而是继续从政,也许他会走得更高更安全,而不是今天这样身陷囹圄。所以,一个错误的用人,不仅是害了企业,也害了这个人。
拿来主义彻底失败
贯穿华晨发展史的要素还有一点:技术上的拿来主义。
这是仰融和祁玉民为数不多的共性。仰融时代,华晨从雷诺拿技术,而彼时的奇瑞、长安、吉利已然开启了正向研发,打造自己的发动机系列。
祁玉民更甚,他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Dream car:“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
甚至于,祁玉民还曾建议国家把合资品牌的产品限制在15万元以上,防止合资下探,让自主龟缩在10万级以下的市场,井水不犯河水,避免自主因技术不够无法与合资相抗衡。现在看来,是何等的可笑。
所以,在祁玉民执掌华晨的十余年里,华晨系自主品牌一直拿宝马淘汰的设计、技术,并以此为卖点大打“外资技术”牌,而自身鲜有技术突破和积淀。但与此同时,扎根新能源核心三电技术领域的比亚迪因电动化的到来开始飞跃;完成“蛇吞象”壮举的吉利吸收着源自沃尔沃技术的养分,不断反哺自身;奇瑞,十年磨一剑的地表最强1.6T、2.0T发动机先后出炉,长安的蓝鲸NE动力平台也为旗下轿车、SUV提供了实力强劲的三大件。
反观华晨系,从中华V3、V5、V7到华颂7,都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比如中华V系列,发动机用宝马的,就连外观设计也要抄袭宝马。可惜的是,光有宝马的形,品控、调校却没有宝马的神。
简单的“拿来主义”在随后激烈的竞争中,弊端立显。比如SUV浪潮之下,中华V3在2016年底月销破2万后,在新一轮消费者升级中迅速落败。当吉利、长城、长安很快跟进产品、换代车型,V6、V7直到2018年才上市。
“拿来主义”的小利小惠,终究导致了今日华晨中华的惨败。
华晨的警示
以华晨为鉴,无论是对于当下的一线自主,还是同样有着浓厚国资、央企背景的一汽、东风,又或者和华晨走同样路线的一汽,华晨的落魄无疑起到了警示作用。
一方面,相关部门用人上一定要“术业有专攻”。特别是车企一把手,他们的管理风格直接决定了车企的特质。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汽车市场,一定要大胆启用有新思维的管理者,要具备革故鼎新的勇气和魄力,而不是因循守旧,一味关注政绩,活在合资公司的短暂利润中。如果接班仰融的是更懂汽车的竺延风或尹同跃们,华晨断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另一方面,核心技术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车企切不可贪图“拿来主义”的一时利好,只有技术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不受制于人,永葆卓越。
否则的话,华晨就是前车之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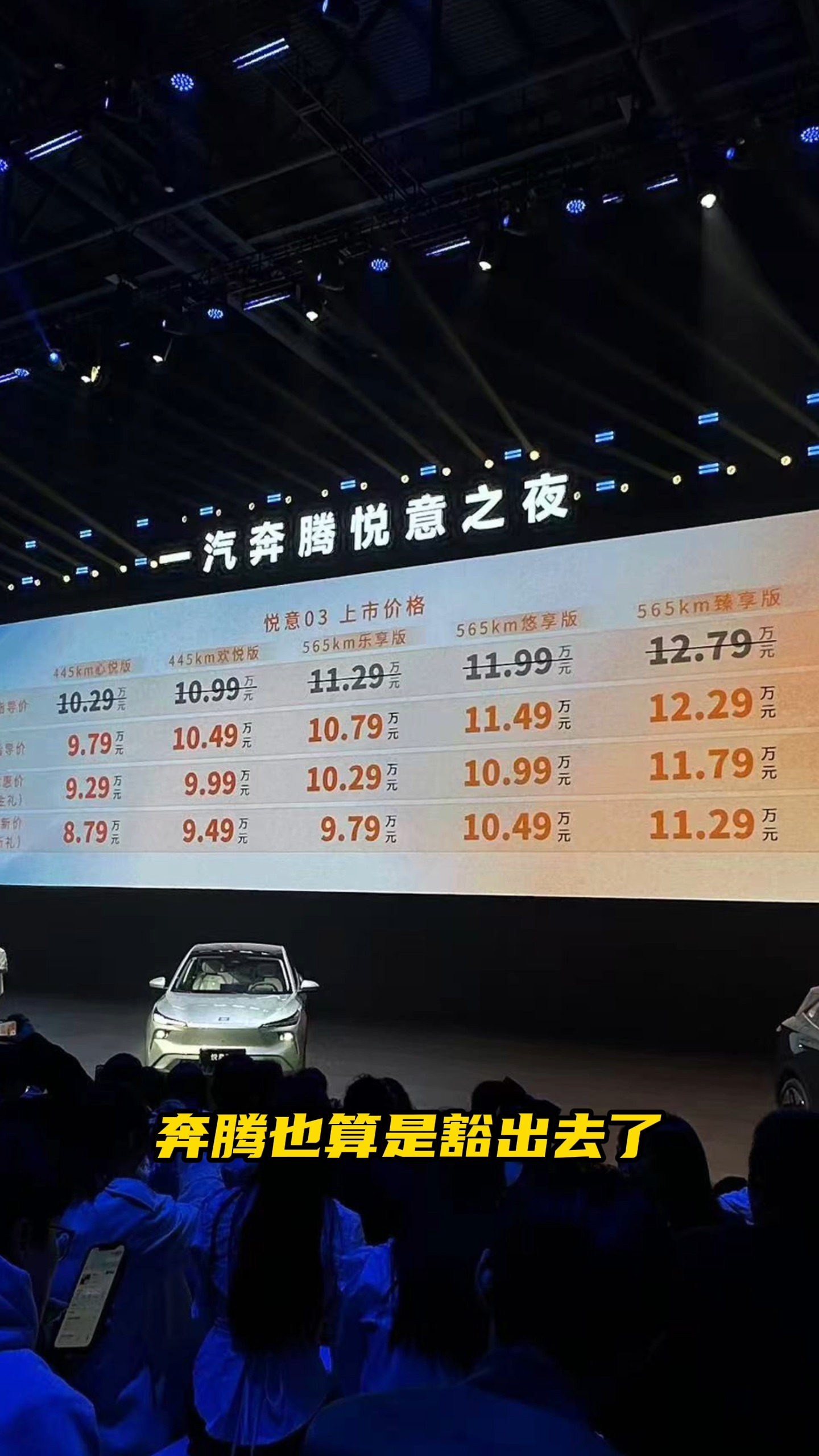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0157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0157号


网友评论